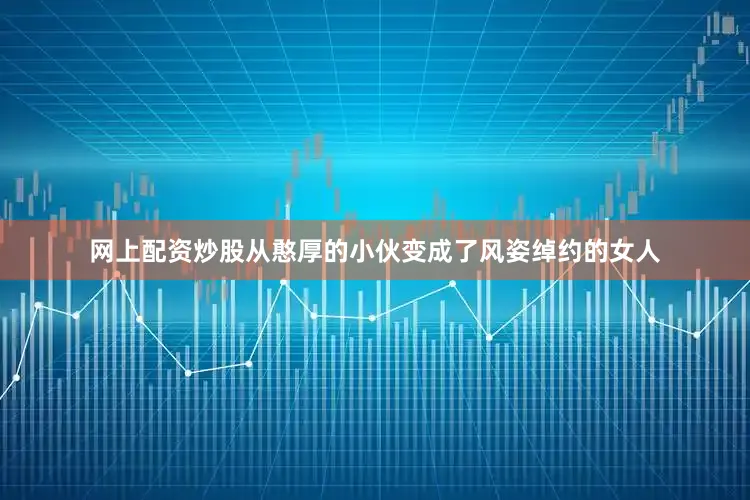
冷元华
金苇河是见证一个乡村渐变为一座城市的守望者,扯上它家乡扬中便有伤筋动骨般的疼痛;它又是一位匆匆而来、默默离去的过客,身后留下的一串串泥土气息久久未能散去。
故乡的小河甚多,而金苇河却是我见到它出生的河。它的前身是连片的沃腴农田,承载了乡土人一生的酸甜苦辣。因为排水和灌溉的需要,它的其中一段身子被划了长长的一刀,水便自然地涌了出来,从此它华丽转身,从憨厚的小伙变成了风姿绰约的女人,水灵灵的,穿着一条短裙迎风招展。
展开剩余76%金苇河本没有名,是我给起的,其实也不是我起的,或许它天生就应该叫这名。像所有的小河一样,河的两边总有杨柳婆娑的身姿。缓缓流淌的水流与一群群鱼儿经常荡漾在油菜花的早春或是夏季的傍晚。这是一个多情而充满梦想的季节,少年的我周末经常徘徊在它的周围,端详小鱼游来游去,惊愕于它的妩媚多情,便作文一篇《故乡的小河》,受到语文老师的啧啧称赞:“写得不错,修改一下,你可以投稿给报社试试。”
等待报社消息的日子,便是和金苇河的流水一样,希望慢慢流走,失望接踵而至。然而,一颗文学的种子却丢进了河里,慢慢蕴育,待来年的某个早晨,水面上探出的几片菱叶,逐渐舒展开来,悠闲地随波飘荡。
金苇河并不长,可以一眼望到头,笔直的身躯有时如同一位猛汉,架在岸边的水泵更像一门大炮,随时准备发射,给金苇河又多了一分阳刚之气。从此,每到农耕季节,金苇河的两边便是喧闹的集市。大人们忙着收割,小孩子也帮着拾穗,小渠里灌满了欢快的浊水,它要一路畅游这广袤的田野。
金苇河,活生生流淌在我的身边,又静静地收藏进我的记忆深处。那里有母亲劳作的身影,有我脚被割破的血迹;有队长催促的哨声,有小伙伴打闹的啼哭。它集宁静而又热闹、温柔而又豪迈于一体,不断演绎着四季的交响乐。
城市张开血盆大口,不断地吞噬一片片农田和野沟。金苇河未能幸免,在某个寒冷的季节收到了法院的“判决”,施以“宫刑”。它被抽干了全部积水,大大小小的浮游生物为它殉葬,从此阴阳两隔。几个月后,它改成了下水道,上面铺成了一条城市主干道,取名金苇路。从此那条充满生机的小河失去了生命,城市的繁华便是它的坟墓。
我小心翼翼地走在金苇路的一侧,再也看不到它安静的模样,感受不到它水灵般的呼吸和在它身边垂钓的惬意。它转世成了一头老黄牛,所有的人和物都骑在它的背上,不断地碾压,它的胃里接纳了各种各样未经处理的污水,直至口吐黑沫,把附近的明珠湾变成了黑臭河,最后功成名就,因臭而闻名全国。
污水直排、河道换水的捷径终究不是解决了污染,而是转移了污染,就像城市里不断遮人眼目的围墙,围住的是你的视野,那不堪的丑陋并没有消失。
经过督察整改后的明珠湾虽然恢复了原有的生态,但是消失的金苇河早已被他人忘记,仿佛它从来没有来过这世上一样。然而我却时常想起它的模样,这条无名的小河虽然没有苏州河迷离、鬼魅,但是它清新脱俗,单纯得没有一丝杂念,它的德行远超过一般的俗人。这条河的生命很短暂,却留下了我驻足的身影、梦想的起源和尘封的记忆。
金苇河,我心中的河。
此文荣获第二届“春光杯”当代生态文学大赛二等奖,最初收录于《2025年中国生态文学获奖文选》。
作者简介:冷元华,男,江苏扬中人,镇江市老年大学作家协会会员、镇江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网》会员。《纪检监察在新形势下的“为”与“不为”》获得镇江市国资委“国资清风”反腐倡廉征文一等奖;《灵秀长山书法画卷》入选由镇江市作家协会等单位主办“大美丹徒灵秀长山”主题散文作品;《故乡的金苇河》荣获第二届“春光杯”当代生态文学大赛二等奖;《扬中的味道》获得“鲁迅杯‘文学照耀中国’全国华语文学大赛”三等奖;《寻求阳光灿烂的日子》获第四届“最美中国”当代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1985年的那场高考》、《一滴水的情怀》分别入编《当代文学家·丽春卷》、《芙蓉国文汇》第二十卷。
发布于:江苏省全国配资公司,炒股加杠杆app,股票配资推荐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